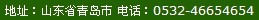|
年秋,我考入山东徐州(时属山东,年归属江苏)二中读初中。那年,我十三岁,正是懵懂少年,人云亦云的时代。不过,即使今日年届八旬,我几乎仍然常常是人云亦云,罕有标新立异之论。 二中建筑在老城东北部的孔庙(黌学,亦称学宫)旧址上。大门前原有一条围绕学宫的河,早已壅积成一片池塘,池塘南边隔街有一座绿碧辉煌的琉璃瓦的九龙壁,其东侧不远处还有一座形似鹏鸟展翅欲飞的奎星楼。奎星,二十八宿之一,主文运。后来,池塘被填为平地,九龙壁被拆除(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学生也被组织起来以义务劳动之名兴高采烈地参与了这些事)。奎星楼不久后也不翼而飞了,附近只留下“河清路”之空名,河水只能存于想象之中了。而黌学巷、文学巷、奎东巷之名也罕有人去想其来历了。那时,城里有许多池塘和水井,后来几乎陆续都被填平了。 孔庙大门(棂星门)及其东西两侧之礼门和义门早就不见,只留下一块刻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在此下马”几个大字的下马碑。二门已被改作教师大办公室,门前是半规形泮池,砌以洁白的石块,池上有三座并列的小石拱桥,环以石栏杆。池水清浅,游鱼悠然;夏日睡莲绽放,清香沁人。科举时代把进学(考中秀才)叫做“入泮”,此之谓也。后面便是庞大雄伟的大成殿(已被当做大礼堂用),殿前有广阔的平台,可坐二三百人。平台前是浮雕精美的飞龙阶陛。出于对龙的敬畏和对珍贵文物的爱护,没有人去攀爬它,而是从两侧的石阶上下。大殿后是已被当作实验室的明伦堂,堂前平台一角有一株根生的唐槐,枝繁叶茂。其南有一块巨大的玲珑剔透的八音石,叩击它的不同部位会发出多种不同的声音。”八音”,古代称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箫管)匏(笙竽)土(埙)革(鼓)木(柷敔)八种乐器为八音。大殿东西两侧的廊庑、斋房等已改建成两座东西相望的红砖二层楼房,这便是我们的教室所在。这里深藏着我们少年时代的种种记忆。然而,这些建筑正在随风而逝,我们这些当年的青衿学子也都垂垂老矣! 年代初,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欣欣向荣,却又政治运动不断,教师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也一再听到某校某老师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捕····教师惊惧而学生兴奋。学生白天上课,晚自习前跳集体舞,唱歌。当时,教育学苏联,记得语文课本上有篇题名“杜伯洛维娜访问北师大附中”,讲课的老师说,他叫文北垣,“垣”和“坦”读音和写法都不一样。又说“娜”读“挪”,不读“那”。我们虽觉别扭,却谁也不敢质疑。后来,我查老字典比如《康熙字典》《词源》,“娜”果然只有“挪”一个读音,“那”的读音新字典才有,还特别说明是译音用字,多用于女人姓名。可见老先生只是接受新信息迟点罢了。还有班主任胡老师,满口无锡话,早操点名时,学生也不知他点的是谁,他便按座号从排头到排尾一号二号三号点得飞快,同学也便纷纷答到,点得比别班都快。他在语文课堂上把“打猎”读成“打蜡”,同学哈哈大笑,说他错了,他反复解释学生也还是听不明白。后来我终于明白无锡人“猎”“蜡”读音不分,是方言有差别而不是胡老师读错了。学生对他意见很大,他却执意不改,后来终于调回南方去了。 教英语的萧老师湖北口音很浓重,有些同学喜欢模仿他的湖北腔。王国平在课堂上偷偷给他画了幅漫画头像:有几道横纹的额头上覆盖着稀疏的短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昂着头,张开大口讲课,画得惟妙惟肖,神气活现。我相信萧老师本人看了也会忍俊不禁。还有一位代理班主任的计老师,人很高大,鼻直口阔,极有个性。他服装考究,颇有学者风度。他喜欢把自来水笔插在上衣的右边胸袋里,还用右手比划说:这样取笔比较近,也更方便。他英语口语流利,时常有苏联专家朋友来看他,同学对他都很敬佩。他有时还拿一些英文书刊给我们阅读,让我们试着翻译一些短文。我们班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晨会上他严厉批评调皮学生:再调皮,我一个“钉子”(借指操行评为“丁”等,不及格)把你钉出去!这些调皮学生也就有所收敛了。后来,计老师调到安徽大学任教去了,同学们还很怀念他。 教平面几何的宋老师兼任班主任,他中等身材,面貌端正,络腮胡子刮得精光,两腮发青,衣着整洁,为人正直善良,教学严谨,一丝不苟。他在课堂上常讲两条直线相交,每逢讲到“相交”时,前排有一位高度近视的同学便悄悄接话说:“我吃”。一次下课后,他跟我说:这堂课我吃了十几根“香蕉”。他是一位非常刻苦好学的学生,后来上师范做教师,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特级教师。王曾平在回忆录《大路朝天》(澳门生活杂志社,年出版)中写道:“文革”中他从市公安局调到母校二中教书,初到校内忽然见到正被隔离审查、遭受羞辱的的宋老师,近在咫尺,却相逢不敢也不能相认,只能眼泪汪汪。后来听说宋老师解除隔离后才知道妻子自杀,家破人亡了。那些年月,遭此不幸的老师、同学不少,令人只能扼腕叹息了。 艺体组教师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之地。教体育的杜老师对学生极为严厉,却往往在疾言厉色训斥学生之后又恳切自责,说他脾气杂毛,对不住你,恨不得自打耳光。学生即使铁石心肠,也不能不被感动得鼻酸眼涩了,虽然怕他却不恨他。每到雨天放学时,他身披雨衣站在场地一角,瞪圆双眼盯住学生,不准学生踏坏场地——那年月操场地面没有水泥,连煤灰渣也没铺。他像一尊操场的守护神。这样的老师在“文革”中自然少不了吃苦头。教音乐的郑培心老师,面相白净大方,颜值很高,有一副明星相。他极喜欢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他改编民间曲子,创作了《徐州小景》《徐州八板》等胡琴曲,颇受欢迎。又同友人曾亚夫先生(联合中学即今八中音乐教师)合作,发掘了久已失传的古筝并加以改良,这是他对保护民族古乐的重要贡献。他喜欢柳琴戏,与一些著名柳琴戏演员是很好的朋友。他教学生唱和排演柳琴小戏《喝面叶》。他会多种乐器,尤擅口含两只口琴吹奏。他的学生王士玉成了全国闻名的胡琴演奏家,学生蔡敬明以吹笛名噪大江南北,并曾远赴亚欧多国演奏,广受欢迎。他还教我们用竹木蛇皮马尾等自己制作二胡,一时间课余只听琴声吱吱扭扭,好不热闹。我也制作了一把二胡,只可惜我后来并没有学会拉琴,琴也送给了一位亲戚。学校还有几位绘画名家。张之仁先生,南通人,多才多艺,以山水画和草书知名于世,他不仅教美术,还教语文,讲起课来,口吐莲花,令人心往神驰。他担任过语文教研组长。后来出任市文联负责人,筹建市国画院并任院长。我曾几次在张府聆听他讲绘画与草书,多受教益。刘梦笔先生擅花鸟,王仲博先生自称小沛人也,以地理老师兼善山水和大草,名闻远近,身后萧条,近年画名复振。孙彤云先生,以生物学老师兼善绘事、医术。比我高一年级的叶宗镐极喜绘画,后来师事傅抱石先生,多年专心绘事,终成著名画家。 二中许多老师都喜欢京剧,既能清唱,又能粉墨登场。他们曾在学校合作演出大戏《打渔杀家》,杜老师领衔主演萧恩,宋老师反串萧桂英,二位曹老师分饰倪荣、李俊二豪家,张老师、董老师等分饰教师爷和众家丁等,生旦净丑,角色齐全,唱念做打,精彩纷呈,唱得有板有眼,演得像模像样。台上台下,其乐融融。实乃校园一时盛事。 这时学生课业负担不重,来校时只要带着简单的书包(许多学生仅用包袱皮包书,或用一根带子把几本书簿一捆),住校生把几本书挟在腋下就进教室上课了。除了上课,每天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学校图书馆(建于尊经阁旧址上)有许多藏书和报刊,又随时购进新书,供同学们课余在阅览室翻阅或借回家阅读。我在初中阶段便借阅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和当时流行作品。学校很重视文体活动,篮、排球队、体操队、舞蹈队、歌咏队、腰鼓队、美术组、学科活动组等,都搞得有声有色,让同学们自由地发展兴趣和特长,有利于各种人才的成长。学生会干部(有的还是市学联干部)、青年团(当时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年才改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都很活跃,经常组织各种大小活动,发展成员。班里有些学生是干部子弟(他们来自干部子弟小学),似乎有点优越感;也有不少同学家庭经济生活比较困难,申请领取不同等级金额的助学金,有点自卑。有些同学特别是有些农村同学年龄较大,其中有的已经结婚甚至有了孩子,也有城市学生做过学徒、店员又回来上学,很自然地形成一些不同群体。我在班里也有几位好朋友:杨克芳、武仲华都来自农村,是团干部。毕业时,克芳去了沈阳炮校,成了军官,后来失去联系;仲华回乡务农,酷爱写作,多愁多病,不幸早逝。曹景忠,后来考上大学,终于成了数学教授。程伯良,在煤矿工作。我班同学后来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军官、运动员和教练、工程师、党政干部····也有被错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受尽苦楚。几十年来,尘海浮沉,饱经沧桑。许多学友天各一方,此生若有缘重逢,真想道一声:故人,别来无恙!如今,有六百余年历史文化底蕴的二中面临拆迁,母校古雅的姿影再难寻觅。面对云山夕照,只想唱一曲:夕阳山外山······ 赞赏 长按白癫风区别白癫风怎么医治
|
当前位置: 徐州市 >那时的学校遥记徐州二中的初中生活
时间:2018/3/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2018年江苏徐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公开招
- 下一篇文章: 厉害徐州45所学校76名教师上榜教育